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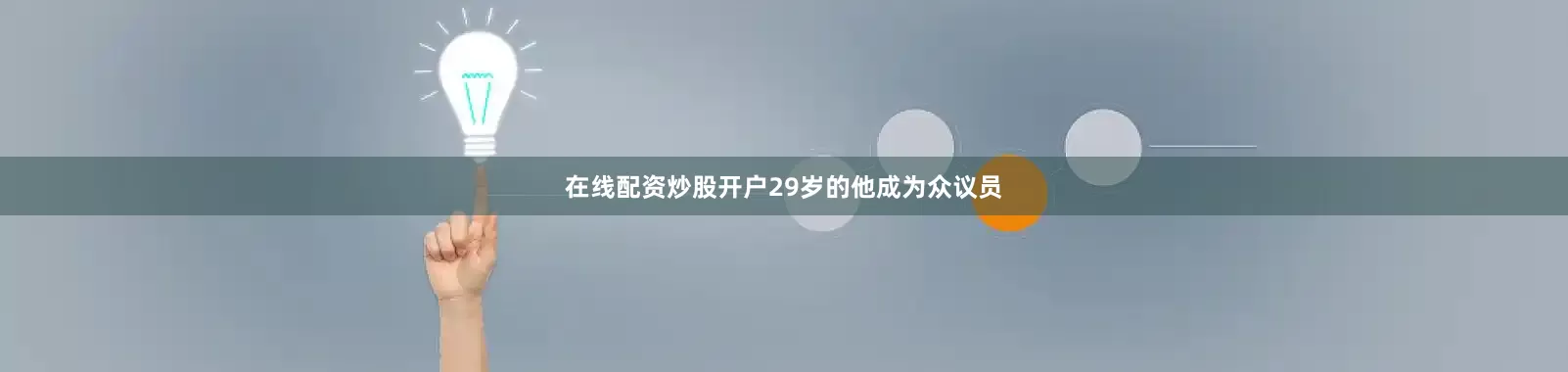
东京的仲夏,空气里潮湿得像是要滴水。8月15日,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的追悼仪式在肃穆的音乐中开始,外界把目光都投向演讲台上的那个人。他说了“悔恨”,语气不重不轻;他也谈“教训”,主旨是要铭记。但台下不少人心里明白:这不是一份经过内阁审议的官方谈话,只是首相个人选择的字句。媒体很快用“轻飘”来形容这番话,原因不难理解——没有提“加害责任”,没有明言“侵略”,也没有那种能写入教科书的清晰措辞。对于这个走上权力巅峰不到一年的人而言,这一天像一道横在面前的坎。

变调的传承
在日本的政治语境中,8月15日的“谈话”是一种制度化的期待。1995年,村山富市在内阁会议上敲定那份著名谈话,明确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与侵略给亚洲带来巨大伤害,表明“深刻反省”和“由衷歉意”,并哀悼所有受害者。这种由内阁统一决议、首相对外宣示的形式,曾经是战后日本面对历史的姿态。

十年后,小泉纯一郎延续这一框架,仍承认侵略与殖民,只是他频频参拜靖国神社,让那份“中规中矩”的文本总带着争议的阴影。再到2015年,安倍晋三的“面向未来”成了关键词,“侵略”“殖民”这些刺痛人的词汇被绕开,他赞同不必“反复重复”老话,同时在历史叙述上留了大量空白。承接、稀释、转向,谈话的力度一节节被卸去,政治风向也随之变化。
在这样的演变上,2025年的节点又出现了一个新的“断裂”——没有官方谈话。早在3月26日,《读卖新闻》就放出风声:为了避免党内反弹,政府可能不发正式谈话。到8月,猜测兑现,首相只在仪式上表达个人“悔恨”,而非内阁定调。这是形式与内容的双重退却,也意味着,原本承接三十年的“习惯”被戛然而止。

人设与现实
说回这个人本身,他并非出自政治的真空。石破茂生于鸟取县的政治家庭,父亲是当地知事。少年时代,他在家里见惯了政界的门道,大学修的是法律,毕业后先去了银行,算按部就班。真正踏入权力场,是1983年,受田中角荣的影响,29岁的他成为众议员。那一代人的政治启蒙,往往绕不开田中的影子:地方利益、派阀均衡、擅长交易的“田中学”。石破也不是例外。

他在党内职位不算显赫,却一路做过硬差:早年分管防务,对军备与安保熟稔;当过防卫大臣、农林水产大臣,也坐过自民党干事长。对外与安全议题上,他时常用直截了当的方式触碰党内主流的痛点。这样的风格让他看起来像“异类”,却也赢来一批认同者。连续四次竞选党总裁失败,还能再次归来,靠的正是这种“拧”,直到2024年9月第五次出战,终于获胜,并在10月1日组阁。
但登顶即是风浪。那会儿,自民党丑闻连缀,支持率一度跌到谷底。他选择用地方振兴与防灾治理作为开局主题,试图把注意力从疑云挪开。只是经济形势不给面子:通胀攀升、民众信心不足,内阁支持率从组阁时的四成多一路下滑,很快跌破三成。到了今年上半年,这条曲线几乎没有回头的迹象。

少数派的困局
真正的打击在7月20日。参议院改选,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盟遭遇惨败——自民党席位从52席降到39席,公明党从14席缩至8席,两家加起来过不了半。这意味着,政府沦为彻头彻尾的少数派内阁,任何法案的通过都要看反对党脸色。第二天,他还是选择正面迎战,在7月21日公开表示留任,继续推进政策。但真实的政治场景,是党内会场争吵不断,支持率又往下拐,到8月已跌至二成出头。
这时候观察日本政治,有几个结构性因素值得提起。其一,参议院不能解散,少数内阁意味着在上院受制约的时间更长;其二,自民党与公明党长期协作,维系在共同立法议程与选举互助,但一旦席位流失到一定程度,盟友也会谨慎保持距离;其三,派阀政治虽因“丑闻”而收敛,却并未消失,首相需要平衡的内部压力反而更复杂。
历史与教科书
更敏感的,是历史叙述的战线。自民党保守派在过去十余年里不断推进一套历史观:在中学教材里把“南京大屠杀”改称“南京事件”,回避具体死亡数字;在“慰安妇”问题上强调民间动员甚至“自愿”,淡化政府与军部的责任;在冲绳战役的叙述中,轻描淡写本土部队逼迫民众自尽的情节,更多把矛头指向美军轰炸。现实中,讲述受害者故事的出版社屡屡遭到右翼围攻,甚至被逼到破产;课堂上坚持讲述史实的教师,会遭到停课处分。历史,不只是过去的记忆,更被当作今天的政治资源。
安倍时代的“定调”,在许多人看来已将“道歉外交”封存。2015年的谈话被视作“终结”,因此保守派认为无需再开口。到了石破上台,这股力量并未减弱。他早年对安保政策的批评,曾让部分人期待他会推动更有力度的反省,但掌舵之后,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冷硬的现实:没有内阁共识,就没有谈话文本;谈得重了,党内裂痕会更大;谈得轻了,海外不买账,而国内又未必满意。
节点与沉默
8月15日的个人表述之后,另一个日子也在日历上逼近——9月2日,日本签署降书80周年。首相本有意在这个节点发一份个人见解,沿着“悔恨”的基调再往前走一步。但右派反对迅速拧成绳,反对声高到难以忽略。这一次,他把想法咽了回去。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对外说,政府将“适时作出判断”,话讲到这,已经等同于没有决定。后来事实也证明,“适时”没有到来。
外交上的回响不久便显现。对中国而言,日本侵华时间长达十四年,从1931年的九一八到1945年战败,数以千万计的家庭破碎。今年北京举办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,邀请各国共同缅怀。对比之下,日本方面未发官方谈话,显得格外冷淡。外交部发言人直言不讳:历史认知问题影响邻国互信。这句话在东亚,永远不只是外交辞令,它会穿透媒体与公众的屏障,迅速在民意层面变成真实的情绪。
同台之人,不同抉择
如果把村山、小泉、安倍与石破同置一台,能看出日本政治在历史问题上的几道轨迹。村山的时代,社会对反省的期待与国际环境的压力叠加,官方谈话具有开创意义;小泉在保守色彩与制度惯性之间保持一种微妙平衡,文本继续承认,象征行为却不断撕扯;安倍则试图“向前看”,强调不要重复旧话,从语言策略上收回承认与道歉的地盘;而石破面对的是已被重塑的党内共识,别说“加码”,连“维持”都难。他的个人倾向——对安保的直言、对历史的更强反省——曾构成他作为“异类”的标识,但少数内阁与席位崩塌,让他无从挥洒。
在政治学意义上,这是典型的结构约束压倒领导人偏好。首相的权力并非总统式的单点控制,内阁制下的政策输出要通过党内与阁内的多重闸门,尤其是在日本,派阀虽弱而未灭,执政联盟本身也要求妥协。8月15日的“个人表达”,不仅是文字轻重的选择,更是制度路径的产物:当无法形成内阁一致,首相能做的就只有把公式性的表态压缩到最小风险。
选举的影子
把镜头拉回7月,参议院选举失败的后果一直拖拽着内阁。自民党从52席跌到39席,公明党从14席跌到8席,数字背后,是反对党可以联手在上院阻滞几乎所有争议法案。少数内阁的日常,是每一项议程都要到野党那里“试水温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任何可能引发外部强烈反弹、内部重新洗牌的动作,都被迫推迟。党内一拨人公开施压,要求首相为败选负责;另一拨人希望苟住时间,等经济指标稍有起色再作打算。首相7月21日的“继续推动政策”的表态,并非没有勇气,而是尚未找到替代路线——然而时间不等人,民调到8月已经掉到二成出头。
关于制度的几句话
这里有几句“小科普”,有助于理解这段轨迹。日本首相的“谈话”分两类:一种是内阁审议通过、作为政府立场对外发布,约束力强;另一种是首相个人在场合中的讲话,政治效果有限但能释放信号。教科书审定由文部科学省负责,出版社先编写再送审,审定意见可以对措辞与史实叙述提出“修正要求”,这给了政治力量影响历史叙述的空间。至于参议院,它不以“解散”作为政治危机的出口,选举周期固定,这让少数内阁面对的阻力具有顽固的时间长度。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盟,是战后日本政坛最稳定的“政党合同”之一,但并非牢不可破,当选票不再相加,政治账也会迅速重新计算。
信念与博弈
石破茂的故事,很难用“失败”或“退缩”一词简单。他出身地方,懂得如何与地方利益对话;早年在安保议题上的直言,塑造了鲜明的个人立场;经历四次败选才在2024年9月赢得党总裁,10月1日组阁,那种逆风翻盘的精神不常见。但到了2025年,经济压力、选举挫败、党内保守派的合围,把他的空间压缩到窄若刀锋。他在追悼仪式上用了“悔恨”,这在今日自民党的语境里并非无意义的词;与1995年的“由衷歉意”、2005年的承认相比,力度不可同日而语。9月2日那次“计划中的发声”,终究没有成形,也昭示着一个事实:在权力与信念之间,他更多时候要为权力的存续付出信念的折扣。
“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”在东亚政治里,这句话既是历史的箴言,也是现实的考题。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每一次表态,都会折射国内政治的配置与国际环境的起伏。村山、小泉、安倍、石破,是同一道题的不同解法,而各自背后的条件也大相径庭。对邻国而言,期待的不只是辞藻,而是能写进制度与教育的共识;对日本社会而言,如何在多元叙事中找到能承受外部检验的版本,考验的不仅是政治家的胆识,还有制度的韧性。
东京的夏天很长。等到秋天风起,政坛的账还要继续算。少数内阁能否挺过议会的层层关隘,经济能否止跌回稳,党内会不会有人接过“责任”的话筒,这些问题都会反过来塑造下一次在纪念碑前的发言。到那时,选择用哪个词,停在哪个逗号,可能仍然是政治最真实的分寸。
金色配资门户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